-
压轿
普通类 -
- 支持
- 批判
- 提问
- 解释
- 补充
- 删除
-
-
压轿
压轿
刘成章
陕北的花轿,现在是早已绝迹了,早已用汽车、拖拉机代替或者根本不要它了;但我小的时候,却常常能见到,常常给我带来无限的乐趣。
每当花轿过来,必有吹鼓手领头,咿咿哇哇地吹着;必有迎亲的以至送亲的妇女 ( 称做 " 硬姑 ") ,穿得花枝招展,骑着牲口,以花轿为中心,走成长长的一串。这支队伍的两侧,也必有娃娃们跟着,跑着,他们有时会不小心被石头绊倒,灰土抹靥地爬起来,胡乱地拍上两把,跟着又跑。这娃娃们里头,往往就有我。
要是花轿到了娶亲人家的埝畔上,噼噼啪啪地放起炮来,我们就更乐了,没命地抢那落在地上的哑炮。有时可以抢到好几,个,还带着捻子,我们就再往地上东瞅西瞅,拣起一个还没熄灭的烟头,顾不上再看花轿,走到一边自个儿放起炮来。
看蒙着红盖头的新媳妇下轿,看拜天地,那自然是更有意思的,我们就使劲往人缝里钻。被挤撞了的大人,无论脾气多么不好,此刻也不会骂我们,也会把我们让到前边去。等这一套结婚的礼仪全进行完了,人们入席吃起来,我们又会凑到 ? 听媳妇身边,而新媳妇往往又会悄悄地给我们手里塞一块冰糖,是我们受宠若惊地拿着跑开了。至于新媳妇穿着什么衣裳停么鞋,她的脸蛋是俊还是丑,我们却是不怎么注意的。獭暴一是为了凑热闹。热闹上这么一天,晚上睡得极香极香,有时候,还会笑出声儿来呢。
使我十分高兴的是,有一年,我的一个叔叔也要娶媳妇了。那期间边区刚刚进行了大生产,到处丰衣足食,喜事都操办得非常隆重。我家也不例外。我记得,几乎是一年以前,家里已忙活开了:打新窑,喂猪,做醋 -- 到了临近婚期的时候,推白面呀,磨荞麦呀,压软米呀 ...... 样样项项,真有忙不完的事情。我年纪小,重活干不来,零碎活却总要插上手去。我高兴啊 !
喜日,鸡叫二遍,全家人就都起来了,都穿上了新格崭崭的衣裳。到鸡叫三遍,前来帮忙的亲戚也都陆续进门。于是,大家烧火的烧火,切菜的切幕,扫院子的扫院子,家里家外,灯火辉煌,忙成一片。接着,踏着上午暖堂堂的阳光,亲友们,拖儿带女,在相互问好声中,也都上了硷畔。
花轿要出发,人们喊叫着,要我家的一个男娃娃去压轿。所谓压轿,就是坐在去迎亲的轿里,及至到了新媳妇的娘家,才下来,再让新媳妇坐进去。这是陕北的风俗,不能让花轿空着。我一听,高兴得简直要疯了,呼踏踏跑过去,就要上轿。谁知管事的大人硬是不让我上,而把我的堂弟推进轿门。我于是躺一在地上,打滚搏躐地哭闹起来。
他为什么这样 ? 为什么不让我去压轿。
尽管只有六七岁,我却联想着平时听到的一些事情,心里倏地明白了。原来,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;我一岁的时候,爸爸便死了,当时妈妈很年轻,过了几年,她后走到此,把我带了过来。平时,一家人对我还好,所以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;而在这种关键时刻,在堂兄弟中,虽然我的年龄最大却不让我去,事实上的不平等表现出来了。想着这些,我委屈透了,躺在地上越哭越厉害,别人拉也拉不起来。
为我历尽艰辛的妈妈,使我至今一想起来都不能不下泪。她当时看着这个场面,一定极度伤心,以至没有勇气走到人们面前来,诙哄我两句。我猜测,那时候妈妈或者在炸糕,或者在洗碗,她的泪水花花的眼睛抬也不敢抬一下。多少年来,每遇到伤心的事情,她总是这样。她不喜欢把自己的辛酸讲给别人,哪怕是自已的亲生儿子。那时候,我的每一声哭嚎,都像在她心上扎了一刀啊 !
就在这种情境下,一个邻家姑娘走上前来,双手拖起脸上满是泪水泥土的我,跟管事的人力争,要叫我也压轿去。她名叫秦娟,比我大十岁,梳着一根长长的单辫子。她父亲是卖瓜籽花生的。我常见她每天都起得很早,不是拣蓝炭 ( 煤碴 ) ,就是和弟弟一块抬泔水。
秦娟动了感情,高喉咙大嗓子,争得面红耳赤,但终于在众口一词的情况下,没有争得任何胜利,眼看着花轿抬走了。她气鼓鼓的,当着众人的面,忘了姑娘家的娇羞,把搭在胸前的、黑黑的辫子往后一甩,对我说: " 听话,别哭啦。。到了我的那一天,保证叫你来压轿 !" 她这句话,引得人们哄堂大笑。她一拧身走了。她没有坐酒席。后来人们打发娃娃三番五次地去请她,她到底没来。由于这一层原因,我以后见了她,心里便泛溢着一种特别亲切温暖的感情。她也对我格外好,常常从家里拿出瓜籽和花生,大把大把地塞到我的衣袋里。有次来到我家,和妈妈一起做针线活儿,她笑得甜甜的,望着我,让我喊她姐姐。我心里虽然很乐意,嘴却像生铁疙瘩,叫不出来。她佯装生气了,眼一忽闪,头一扭,不再理我。
这年的冬天,秦娟家搬走了。搬得并不远,还在延安市区;但在我当时想,却好像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,难得再见面了。为这事情,我心里很难受了一阵子。我常想她。特别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,更想她。
过了两年,一个傍晚,我在外边耍渴了,跑回家去舀了半瓢凉水,咕噜咕噜就是个灌。忽听有人喊我,扭过头来,却是一个脸盘红扑扑的女八路,坐在妈妈身边。看了好半天,我才认出,她竟是秦娟 ! 妈妈告诉我,秦娟到了队伍上的剧团,当演员了。秦娟兴奋地笑着说,马上要办个喜事,叫我去压轿。我问:
" 给谁办喜事呀 ?"
" 给我 !" 她响亮地说。
" 好 ! 我压 ! 我压 !" 妈妈却笑道: " 别听你秦娟姐姐瞎嚼 !" 她又对秦娟说: " 你当的是八路军,可又坐上个轿 " 妈妈说着笑起来,笑得前仰后合,用手擦着笑出的眼泪,最后好不容易才又吐出几个字: " 像个什么 !"
秦娟脸上虽然带笑,却非常认真地说,她已决定了,同志们也很支持,一定要这么办。她说,不是为了别的,只是为了让我压一回轿。她还说了些什么,我现在印象很模糊,但中心意思是十分清楚的,就是要让我一颗稚嫩的、受到伤害的心,能够得到平复。
秦娟结婚的时候,我去了。我是下午去的,大概怕影响太大,晚上月亮升上山头,才闹腾起来。
穿着灰军装的人们,这个给我塞一把枣子,那个给我塞两个苹果,然后把我领到花轿跟前。花轿不像老百姓那样的,很简陋是用两个桌子腿对腿扎成的,上面缠绕了一些演秧歌用的红绸子。他们嘻嘻哈哈地把我抱进花轿,又嘻嘻哈哈地抬了起来。花轿前头没有吹鼓手,只由三个人拉着小提琴。
那晚月光很好,他们抬着花轿,抬着我,沿着山腰,喧闹、着向秦娟住着的山那边走去。没走多远,忽然有人报告,一个很厉害的首长上山来了。大伙慌了,赶紧把花轿抬到月光照不到的暗处,悄悄地蹲了下来。
过了好大一阵子,看着首长还没离去,闹不成了,大伙正准备彻底收拾摊子;却不料又有人前来报告,说是秦娟亲自找上首长,说明了情况,首长居然笑呵呵地同意这么办了。于是,寂静的山坡,又喧闹起来。于是,人们再一次抬起了花轿,抬起了我。
月光洁白得就像牛奶,而我所乘坐的花轿,红得就像花;花的红颤悠着颤悠着,连同提琴之声欢笑声,连同我的心上的欢愉,浸润开去,于是,牛奶般的月光粉红了,浅红了,大红了,载着花轿载着我,流向山的那边这情景,以后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。
儿时的我,只像一片小小的树叶,这树叶只碰伤几乎看不见的一点儿,却被牢记于心,以至终于引起整坡森林温存关注的颤动 -- 让我压轿。
这回压轿,虽然不在白天,虽然没有吹鼓手,但那红红漾的热闹劲儿,那重若宝塔山、清似延河水的情意,那革命墓砑地的春风般的抚爱,却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。
-
-
- 标签:
- 安塞腰鼓
- 心里
- 语文
- 妈妈
- 新媳妇
- 前来
- 事情
- 秦娟
- 人们
- 到了
- 家里
- 压轿
- 花轿
-
加入的知识群:

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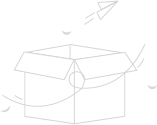
学习元评论 (0条)
聪明如你,不妨在这 发表你的看法与心得 ~